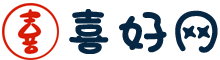我国古文字学泰斗、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裘锡圭先生,因病医治无效,于2025年5月8日1时45分,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,终年90岁。
“实在太突然了!裘先生5月6日住进医院之前,每天都在研究《老子》。他原本打算就‘道’和‘德’专门撰文深入分析,已经写了十来万字初稿,还没来得及改定成文。”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陈剑告诉记者,听闻这一悲痛的消息,他的心里一直空落落的,“在我看来,我国古文字学的一个时代结束了。”
选择古文字,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——简单而又纯粹。裘锡圭最后的20年,从古稀到鲐背,依然是这么度过的。
【最牵挂的两件事】
“我希望能在中心同仁的大力支持下,如期完成我所参加的《老子》注释项目,希望中心今后不断发展,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。”一个多月前,正值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(以下简称中心)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,90岁高龄的裘锡圭录下了视频寄语。
这可以说是他最牵挂的两件事,一是《老子》的研究,他虽视力极度衰退,仍每天钻研《老子》两三小时。二是中心的发展,20年前裘锡圭倾力创建了中心。
古稀之年的裘锡圭把“书桌”安放在了母校,想得最多的仍是心无旁骛、不受干扰地做研究。
马王堆汉墓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。其中,13万余字的帛书简牍是重中之重,有些早已失传,就连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时都未曾看过;出土的《周易》《老子》等古本,与传世的今本有不少差异,具有极高学术价值。
此前由于种种原因,马王堆的简帛一直未能完全发表。而这些简帛出土时都泡在水里,很多地方出现破损,还有大量残片,不少字已无法辨识。能否真实展现2000多年前的历史风貌?以裘锡圭为主编的研究团队奉命于困难之际,历时6年,在2014年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40周年之际,携手湖南省博物院和中华书局,出版了我国首部完整的马王堆简帛注释本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。
“马王堆简帛的整理,使得我们的研究有可能无限接近于当时真实的历史。”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吴振武说。
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是复旦大学文科的标志性成果,201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,在此之前该奖项已空缺14年。
去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,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修订本出版,时年89岁的裘锡圭继续担纲了主编,并完成《老子》新考,令人耳目一新。
在他看来,《老子》中的“善”字,除个别为《老子》特有的用法之外,通常可以按照先秦古书中“善”字的用法来理解。不过,老子用的应该是“能把事做得很好”“能干”“擅长、善于”这类较古的意义。“老子对世俗的仁义道德采取轻视甚至鄙视的态度,‘善’字由于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较晚的意义,尤其是与‘恶’相对的主要指道德好的那种意义,老子大概是不会使用的。多数解《老子》者不明白这一点,往往产生错误的理解,应加辨析。”
【一种“力量”的存在】
作为中心的学术核心和精神领袖,身形瘦削、口音软糯的裘锡圭是一种“力量”的存在,旁人“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”。

他做的往往是大文章,考释一个字,填补大片空白。战国时代商业发达,但在玺印和陶器上很少看到“市”字。裘锡圭联想到,政治分裂可能导致“文字异形”,即同一个字存在多种不同书写形式。沿着这一思路,他先认出了齐国文字的“市”,后来把燕、韩、赵、魏、楚的“市”也逐一辨析,堪称文字学领域的扛鼎之作。
他勇于质疑。《老子》今本有“宠辱若惊”一词,“受宠若惊”正由此演变,可谓由来已久。但裘锡圭研究郭店楚墓《老子》简发现,“惊”其实是“荣”的误读。这句话与“贵大患若身”相对应,后者意为“把大患(死)看得与生一样可贵”,“宠辱若荣”则是“把辱看得跟荣一样可贵”。
他更敢于自我批判。7年前他还发布声明,称自己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“可谓毫无是处,自应作废”,希望通过新作“稍赎前愆”。
裘锡圭被誉为中国古文字考释和文字学理论研究第一人,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。他喜欢和青年学者讨论问题,就算听见“裘先生您说得不对”也不愠不怒,这在旁人看来也许有些不可思议,但这样的切磋场景就是一种日常。
中心主任刘钊教授说,“我年轻时不懂事,常写信给裘先生帮我复印自己找不到的文章,他从不以为忤,每次都及时地把文章寄过来。”
古文字工作堪称“冷门绝学”,数十年来,裘锡圭一直埋首故纸堆,就算术后卧床,也坚持要听经典古籍。
如今,古文字研究“春天”来临,希望能告慰先生。
大师远行,一路走好!
裘锡圭简介:
著名古文字学家、古文献学家、历史学家,第八、九、十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六、七、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。
本文链接:http://www.xihao.site/showinfo-4-13021.html我国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逝世,生前最后日子仍每天钻研《老子》